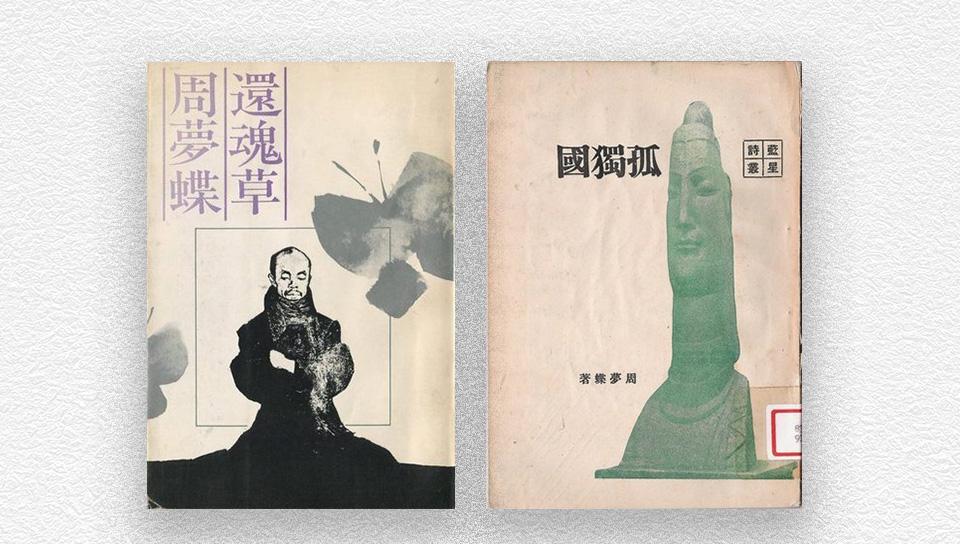示意圖(Image via Shutterstock.com)
《還魂草》輯一「山中拾掇」,輯名之下,周夢蝶引用英國詩人白倫敦(Edmund Blunden, 1896-1974)的詩句「一塊石頭,使流水說出話來」(Speaks, all the dumb shoal shrieks, and by the stone, Water Moment),到了輯二「紅與黑」,引用了小說家哈岱(Thomas Hardy, 1840-1928)的話:「人生如鐘擺,在追尋與幻滅之間輾轉、徘徊」。
第二輯:紅與黑
根據周夢蝶的說法,「這一組詩的誕生,是相當『偶然』的。」1959年3月,偶然間,他在兩本雜誌上讀到兩首文字風格幽豔的小詩〈三月〉,一時心頭癢癢,仿製了一首詩。之後,又寫了〈四月〉、〈五月〉、〈七月〉。朋友C問他是否要將十二月份一網盡,他笑答:「但願如此。」,後來果然成真,寫「月份」的詩,《還魂草》共13首──〈一月〉、〈二月〉、〈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十二月〉、〈十三月〉、〈閏月〉、〈六月 又題:雙燈〉、〈六月〉兩首、〈六月之外〉;《風耳樓逸稿》有11首月份詩。〈三月〉沒有收入詩集,成為「逸稿」,據學者推測,可能是詩人在報刊發表詩作後,再收入詩集時,刪除不理想的詩作4。
至於為什麼第二輯標名為「紅與黑」,可能是詩的內容包括「形而上的『智』、「形而中的『情』」、「形而下的『欲』」。
/
周夢蝶創作月份詩,值得關注,因為「當代詩人以月分為題作詩最多的,當屬周夢蝶」5,所以陳玲玲在與周夢蝶1979年夜間談話後,分析《還魂草》的「月份詩」就很值得細細思考:
〈一月〉描摹「渾沌初開,乾坤始奠」的情狀。
〈二月〉寫「情」。
〈五月〉敘述時代的苦悶。
〈七月〉寫隱者的清趣。
〈十月〉:悼亡。
〈十二月〉:寂寞。
〈十三月〉:死魂靈的獨白。
〈閏月〉:借雙頭蛇之口,抒發對於「自由獨立」、「智慧解脫」的嚮往。
〈四月〉描寫「強暴」:
沒有比脫軌底美麗更動人的了!
說命運是色盲,辨不清方向底紅綠
誰是智者?能以袈裟封火山底岩漿。
總有一些靦腆的音符群給踩扁
──總有一些怪劇發生;在這兒
在露珠們咄咄的眼裏。
而這兒的榆樹也真夠多
還有,樹底下狼藉的隔夜底果皮
多少盟誓給盟誓蝕光了
四月說:他從不收聽臍帶們底嘶喊……
四月是農曆春夏之交,人容易氣血浮動,是犯罪的季節。
第一段只有一行,用「反語」呈現「主題」。
第二段寫「男女之事」,難以名狀,聖人也不知情何以所起,周夢蝶稱之為「命運」,情欲一發,「如四十里之瀑布」,情勢洶湧。可能只有「智者」能抵擋錯誤的情欲──「誰是智者?能以袈裟封火山底岩漿」。至於為什麼「說命運是色盲」,因為一旦心生情欲,即便可能會有酷刑的惡果隨之而來,強暴者也甘之如飴。
第三段正面寫「強暴」。「靦腆的音符群」是「受害者」。「──總有一些怪劇發生;在這兒在露珠們咄咄的眼裏」,可以聯想到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Allan Ekelund)執導的電影《處女之泉》,當備受父母寵愛的少女Karin被兩名牧羊人強暴並打死時,養女Ingeri躲在一旁,出於嫉妒,手中緊握一塊石頭,睜大雙眼看著牧羊人的暴行。
第四段的第一句,借用美國劇作家歐尼爾(Eugene O'Neill, 1888-1953)劇作《榆樹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 1924),描寫人欲橫流的社會風氣,接下來第二句「還有,樹底下狼藉的隔夜底果皮」,泛指「始亂終棄」;第三句「多少盟誓給盟誓蝕光了」指違背誓言。最後一句詩「四月說:他從不收聽臍帶們底嘶喊……」──最沉痛,透露詩人既悲憫又無奈的感嘆。
/
〈六月 又題:雙燈〉這首詩描寫「破戒」,可能是指周夢蝶讀佛經、皈依佛教前的情感掙扎。事後從2011年文學紀錄片《化城再來人》來看,周夢蝶情感豐富,他曾在電影中說:「在我沒有讀佛經之前,曾經晚上到植物園荷花池邊,那個時候滿腦子都是戀愛,看見那個荷花池啊,我就說這個風啊,不要吹,因為說不定啊,荷葉底下有鴛鴦正在戀愛。」
1979年晚上,周夢蝶在「金太陽」講了一個故事:
塾生某,韶秀穎悟。每昏夜散學歸,師於高處輒見其頭頂有光如雙燈,隨與俱行。心竊喜慰,意生必積善而有夙根者。自是,厚卹其家,而於課業,則督責箴砭綦嚴。忽一日,燈乃不復見。亟喚生至無人處,詢以近所作為,得無有不可告人者否?生低首無語,久之,曰:惟曾為某甲作休書云云。師聞而色變,立命索回,嚼而吞之。明日,雙燈在肩,又燦亮如故矣。
這則故事是周夢蝶十一二歲時,聽母親說的。「雙燈」的典故來自《華嚴經》說人一出生就有兩尊神跟著來到人世間,名字分別為「同名」、「同生」,周夢蝶當時認為:這兩尊神可能是連體的,其實只有一個名叫「良知」的名字。
再對照看2021年出版的《夢蝶全集》〈六月 又題:雙燈〉附註引《楞嚴經》,就有連綿不盡的思考餘韻:
「……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婬室。摩燈伽女以大幻術,攝入婬席,將毀戒體。如來知彼幻術所加,頂放寶光,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趺坐宣說神咒。幻術消滅。阿難及女,來歸佛所,頂禮悲泣。」
又接著引述莎士比亞《暴風雨》:
莎翁論情愛:「這裡沒有仇讎,只是天氣寒冷一點,風劇烈一點。」
/
前面說〈四月〉「總有一些靦腆的音符群給踩扁/──總有一些怪劇發生;/在這兒在露珠們咄咄的眼裏。」這一段詩句可以聯想到電影《處女之泉》,如果藉由李安導演曾在訪談中說《處女之泉》帶給他的震撼和啟發,去理解周夢蝶為什麼會創作〈四月〉這樣一首詩,可能更容易理解周夢蝶作品的本質。
李安說他在入學藝術大學那年看了《處女之泉》,大受震撼,這使他後來在執導電影時,「思考一些對人的存在來說至關重要的事」;李安對於英格瑪·伯格曼從根本質疑上帝的存在、處理複雜的衝突──內在和外在的衝突、人和大自然的衝突、人類平凡的天性,還有,透過上帝去解解這些複雜問題的必要性,觀看這部電影,「就像用顯微鏡去觀察人性」,這部電影「本質上在講人類的處境」、「人與命運、自然的關係」、「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還有,「善惡在我們心中共存」。(李安談《處女之泉》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5NyNfS6KM)
周夢蝶骨子裡也有這種北歐電影的創作風格──追求純粹的精神層面,不斷尋求「人存在的問題」,所以〈六月 又題:雙燈〉這首詩中的雙燈,源自於周夢蝶母親說的故事,周夢蝶小時候聽母親講這則故事的大意,在於「人改過向善」的勸誡,就像故事中生來有雙燈照亮頭頂的塾生,犯了過錯時,頭上的雙燈晦暗,但只要改過,明亮的雙燈又重新照亮他的頭頂。
《楞嚴經》中,阿難差點受娼妓的大幻術引誘、眼看就要破戒,佛陀敕令文殊師利菩薩持神咒,前去拯救阿難,阿難方才清醒。周夢蝶在又題「雙燈」的〈六月〉詩中,彷彿是在人性的複雜中,感受到「持戒」的艱難;每一次破戒都是來世要重修的功課,每一世為人都有要再來渡過的劫數:
再回頭時已化為飛灰了
便如來底神咒也喚不醒的
那雙燈。自你初識寒冷之日起
多少個暗夜,當你荒野獨行
皎然而又寂然
天眼一般垂照在你肩上左右的
那雙燈。啊,你將永難再見
除非你能自你眼中
自愈陷的昨日的你中
脫蛹而出。第二度的
一隻不為睡眠所困的蝴蝶……
在無月無星的懸崖下
一隻芒鞋負創而臥,且思維
若一息便是百年,剎那即永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