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臺北人》(爾雅出版社)三個中文版本
一、「資本」積累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在其知名的「資本」理論中提到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1
在所有旨在創造和積累象徵資本的轉換技術中,購買藝術品,以及作為「個人品味」(personal taste)的客觀證據,是最接近最無可指責和不可模仿的一種積累形式(form of accumulation),亦即以天然的「區別」(distinction)、個人的「權威」(authority)或「文化」形式出現的,獨特的權力標誌和象徵的內在化(internalization)。2
白先勇(1937─)作為文藝場域中的一枚國際知名品牌,本身就是各種「資本」的匯聚與薈萃結果。除了身為將軍之後外,優良的文化教養自不待言。夏志清(1921─2013)曾盛讚白先勇「是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五四運動』到大陸變色以前這一段時期的短篇小說,······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短篇小說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3哈佛大學的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1927─2014)更將《臺北人》視為「當代華文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the highest achieve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y),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則標舉白先勇為「肖像畫大師」(a master of portraiture)。4余秋雨(1946─)將《臺北人》推舉為「被公認對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薰陶濡養意義,並長久被人們虔誠記憶的作品」。5至於歐陽子(1939─)在今昔之比、靈肉之爭與生死之謎的多重二元結構下論述《臺北人》之主題,早已是後輩研究者參考引述的經典範文。
4.jpg) |
1.jp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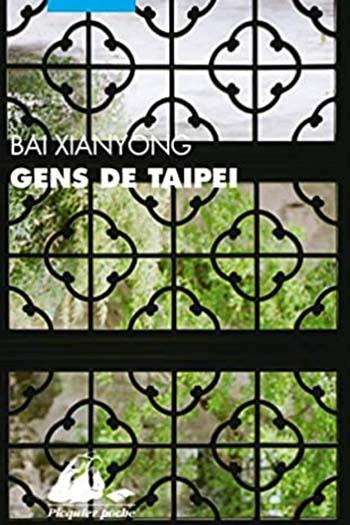 |
(由左至右):晨鐘出版社重排第2版《臺北人》(197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臺北人》英譯本、法文版《臺北人》
1971年,由晨鐘出版社發行的《臺北人》在20世紀中國小說百強中名列第七。《臺北人》集結出版五十年後,陸續有了英、法、德、義、荷、日、韓與希伯來語的譯本,有論者認為它堪比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都柏林人》(Dubliners),匯集了「臺北人」的掙扎、同情、懷舊和哀悼,實為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英文版《臺北人》的編輯高喬治(George Kao)特別在編譯序文中提到翻譯之難,難到讓英譯本比晨鐘出版社的集子晚了十年。高喬治以通用白話(universal vernacular)指稱英譯本《臺北人》中的對話,意指能做到最接地氣的功夫。筆者沒有能力閱讀其他語言的譯本,但想必應該不脫此道。「通用」往往聯繫著「通情」,是「若有知音見采,不辭遍唱陽春」,亦是「讀書有得,冥然感於中,心領神會」。
然而,我們在五十年後新閱、再讀《臺北人》,僅是為了以這些「資本」為自身的閱讀品味加冕,如同以「名牌」加身,讓自己躋升上流?1979年8月31日,白先勇的小說有了第一個「變體」(劉俊語),香港大學海豹劇團將〈遊園驚夢〉改編為粵語話劇上演,其後長達四十年的時間,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及美國(包含英語舞台劇)等地,輪番上演白先勇短篇和長篇小說的「變體」,而改編最多的是第一個被改編的〈遊園驚夢〉。四十多年來,白先勇《臺北人》中的多篇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孽子》的變體則錦上添花,益發點靚「白先勇」的光彩風華。

2003年范植偉主演電視劇《孽子》(圖片來源:中文百科知識)
校園內自然不乏其跫音。從台灣大學的開放式課程舉辦「白先勇人文講座」,到Irving K. Barber學習中心贊助,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系主辦的網路聯播,再到2021年11月20─21日由中國南京大學白先勇文化基金會、南京大學文學院與南京大學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連袂主辦的「白先勇戲劇影視作品研討會」,海內外的學院內/派加持與推廣,不斷強化「白先勇」這塊招牌的資本。不僅大學如此,高中國文課本(如:收錄於《臺北人》中的〈秋思〉和〈國葬〉,收錄於《寂寞的十七歲》中的〈那晚的月光〉,以及撼動眾多讀者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的〈樹猶如此〉,至於〈遊園驚夢〉則被列為補充教材的選文),以及專為高中、大學國文課編輯的「台灣現代文選」一類的書籍(有的甚至有附上教學用的ppt、評量試卷和測驗題本),也收錄了《臺北人》中的〈永遠的尹雪艷〉等作。
上述「教材」讓年輕一輩的學子認識了這位資本雄厚,且發展多元的「斜槓」前輩。市儈地說,台灣媒體甚至以「國文拼高分,多讀白先勇」為標題,直指白先勇為拿分的明燈。整理歷屆考題的出現率,「小說家」排名第一的便是白先勇,其次則是另一位萬人迷,祖師奶奶張愛玲,與中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台灣的國家考試國文考科還出現過白先勇寫的序文(屬於記憶類型題目,無關乎考生文學程度),當真是滿天裡最亮晶晶的一顆星,顯耀的象徵資本。
時移事往,如今,當我們再次翻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應該不會再為荷花池畔碧熒熒如長命燈般的眼神感到困惑,成長於智慧型手機橫空出世後的青春小gay,困惑的應該是這場景怎會發生在一個和政治命名有關的公共場域?不是應該激盪在app的火石電光裡?在情慾漫漶的三溫暖、溫泉和夜店?五十年來男同志的情慾地景早已物換星移,《臺北人》中的「舊時王謝堂前燕」,也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抑或改頭換面、另起爐灶。然而,「白先勇」的象徵資本仍在。
二、懷舊的懷舊
《臺北人》的十四個短篇集中發表於60年代的《現代文學》期刊,小說的敘事背景橫跨1940─60年代。人們因為政治或歷史的因素,逐漸和實體與想像的家鄉產生疏離甚至裂變,如同臍帶被迫翦刈。為了克服這種焦慮,許多殖民和後殖民作家試圖重新想像或重建他們的家園,利用記憶之繩懷舊(nostalgia)。20世紀60年代的台灣在亞太局勢中風雨飄搖,那記憶之繩,歷經了二十多年的上下求索,依舊對於西歸徒呼負負,「反攻大陸、解救大陸苦難同胞」的信念因而歸西。這逝去的,不僅是死絕的池塘春草夢,連階前的梧葉,也喚不回秋聲。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曾言:「所有意識上的深刻變化,就其本質而言,都會帶來特有的失憶現象(characteristic amnesias)。而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從這種遺忘中產生了敘事」。6如若遺忘是一種必然,那麼,身份(identity)是我們從記憶中為自己構建的一種內部敘事的結果,它不僅是一種共同語言、文化和領土的感覺,更至關重要的是真實的,或安德森所說的,想像的祖先(imagined ancestry)。懷舊因而也是思考「時間」的一種方式,不僅是過去的時間,亦是流逝中的時間和未來。記憶的動力在於它的存在總是在當下,即便它在努力尋找過去,而這意味著它不斷地成為「未來」的渠道,因為若不頻頻回首,就無法「想像」未來。
為了避免被曲解和遺忘,白先勇以書寫頂住數十年來紛至沓來的衝擊與詆毀,凌遲般地,一片片削剮他身上的精神原鄉與政治原罪,當然還有對於遺忘的焦慮。他的文字召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中國/文學王國的懷舊愛好者,一玉激起千層浪。白先勇的小說藝術,除了現代主義的澆灌外,更是以中國古典文學為基底而盤旋纏繞的美學「幻」境,「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是扎根於「民國」的災難卻導致的失根流離,「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影影相映,結果卻是灰飛煙滅。
白先勇的作品絕對是雅俗共賞的,但我們恐怕還是得說,在此科技產品當道的年代,除非將白先勇小說改編成線上遊戲或桌遊,年輕人擺脫了考試的利益控制,恐怕只有極少數會繼續like, tag與follow白先勇。說穿了,文青、文中與文老,才是白先勇的鐵桿粉絲(但時至今日,哪個好作家的情況不是如此?)白先勇摯愛的《牡丹亭》商調皂羅袍中,杜麗娘因見「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的後花園,所興發的「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之嘅,這「錦屏人」之於當代社會,焉不可指稱為沈醉在電腦屏幕中花花世界的人類?

父親三部曲(圖片來源:時報出版社)
白先勇在《臺北人》寫下了「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這樣的題辭。幾年前,翰林版主編宋裕曾徵詢白先勇有關選文的意見,得到的回覆是〈國葬〉最適合編入高中課文。白先勇於1994年退休後,念茲在茲為父親白崇禧(1893─1966)寫傳記,終於在2020年完成了「父親三部曲」:《父親與民國》(2012)、《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2014)與《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2020),撰寫期間曾受到歷史學者廖彥博的專業協助。
白先勇在和毛升的訪談中言道:「《父親三部曲》就是企圖還原歷史真相,恢復白崇禧在國軍裏應有的地位,除去許多關於白不實的謠言及污衊」,而「《父親三部曲》可以說是《臺北人》的歷史註解」。白先勇在母喪期滿後赴美求學,一別經年竟是與父訣別。站在父親的墳前,白先勇或許有著「落花猶在,香屏空掩,人面知何處?」之憾,但終究是相看儼然,相逢無一言。
台灣版《紐約客》(2007初版,2017新版多收錄了一篇〈Silent Night〉,香港文藝書屋1974年曾出版同名小說集)是一種回歸真實或想像家園的美學,而《臺北人》是《紐約客》的接駁棧。2018年,在為奚淞《封神榜裡的哪吒》重刊版寫的序文中,白先勇曾說:「我的一腔『幽怨』也都寫進小說中去了」。面對結識超過五十年的同齡人的愁腸百轉,這個自稱「我是永遠的台北人」的耄耋智者,必定早就知曉「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然而世事如曉風殘月,「月輪空,敢蘸破你一床幽夢」?白先勇的小說,尤其是餘音嫋嫋、不絕於耳的《臺北人》,當真是謅一聲哀兩岸,放悲聲唱到老,這幽夢,當真能斷?
《父親與民國》是《臺北人》的註解,年逾八十春秋的白先勇,用四分之一的歲月,為父親寫得「風霜高潔、水落石出」,亦為文學建成「瓊樓玉宇、飛閣流丹」,而後者真的不獨僅靠《臺北人》。2021年白先勇在接受《鏡週刊》採訪時重申:「講白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亡掉了,亡掉了嘛」。屏除泛政治化的解釋,筆者認為,《臺北人》描寫的,不僅僅是官方歷史之外的異生/藝聲(論者所說的「民國史」),更是一部悼亡之書,緬懷已不足以形容,更是白先勇自謂的,「以文學來寫歷史的滄桑」。然而,說到底,終究是「白雲悠悠,江水東流,小鳥歸去已無巢,兒欲歸去已無舟,何處覓源頭?」
然而,我們可以明確知曉,尹雪艷總也不老,白先勇永遠年少。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謝靜國)
註解:
- 經濟資本為可立即直接轉換為貨幣,並可以產權形式制度化的物質資產;社會資本為一種社會關係、榮譽感和受人尊敬的資本,對於贏得和保持上流社會的信任,以及隨之而來的客戶群來說,往往必不可少;文化資本則由「家庭」直接傳遞,且通常表現在良好的儀態、學歷和品味,而文化資本往往建立在經濟資本的基礎上。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ighth printing), p282.
- 原名〈白先勇論(上)〉,後更名為〈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收錄於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附錄。筆者的台灣遠景版小說佚失。
- Pai Hsien-yung, Taipei People, trans. Pai Hsien-yung and Patia Yasin, edited by George Kao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0), description.
- 〈世紀性的文化鄉愁〉,收錄於白先勇《臺北人》(台北:爾雅,2002初版三刷),頁30。
-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91), p.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