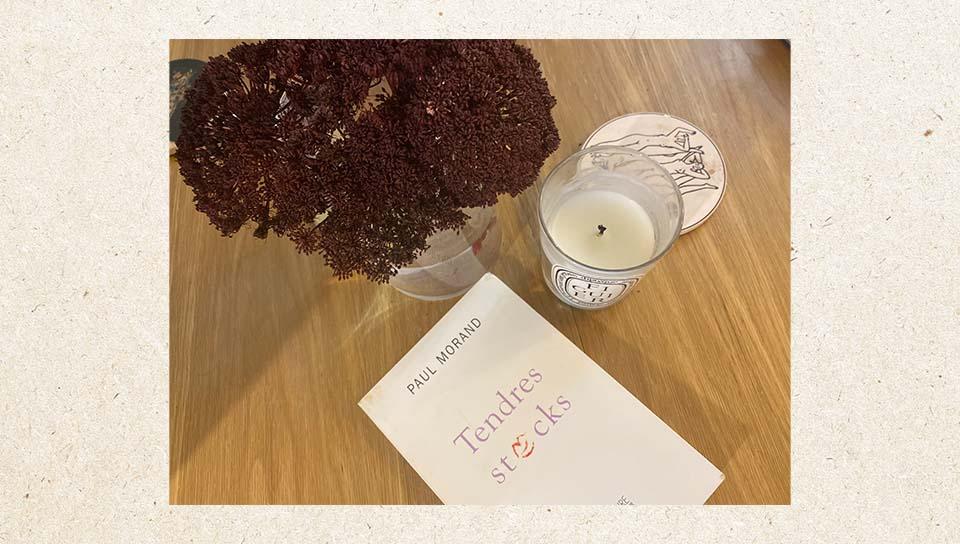保爾.穆杭(Paul Morand, 1988-1976),法國外交官、作家、詩人、劇作家,曾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法國重要文學獎「保爾.穆杭」以他命名。穆杭著作甚豐,出版有一百多部作品,包括了長篇、中短篇小說、詩集、遊記、劇作和專欄,文筆洗鍊,被譽為現代文學風格的開創者。
保爾.穆杭對關心現代文學研究的人來說並不陌生,穆杭小說和中國、日本新感覺派文學、現代主義小說的關係,早已為人津津樂道;穆杭為他的好友可可.香奈兒(Gabrielle Chanel, 1883─1971)所寫的傳記,也為他在大眾間博得知名度。如同香奈兒,穆杭的文風在當時也可稱之為創新時尚。1922年,堀口大學(1892─1981)將穆杭小說翻譯成日文,刊登在《明星》雜誌上,開啟了穆杭小說東亞翻譯的篇章。堀口大學稱讚穆杭的作品以一種「感覺の論理」(感覺的邏輯)組成,開創了新鮮的文體。而後千葉龜雄(1878─1935)在《世紀》雜誌上發表的〈新感覺派の誕生〉一文,又把穆杭和日本《文藝時代》作家群,稱之為「新感覺的藝術」,文中特別提到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溫柔的存儲》、《夜開》(Ouvert la nuit)。
成長於台灣,上海新感覺派的創始人之一劉吶鷗(1905─1940)在留學日本期間接觸了穆杭的作品,1928年,劉吶鷗在上海創辦《無軌列車》,刊登了克雷彌爾(Benjamin Crémieux, 1888─1944)的〈保爾.穆杭論〉(“Paul Morand”)及兩篇戴望舒(1905─1950)翻譯的穆杭短篇小說〈新朋友們〉(“Les Amis nouveaux”) 和〈懶惰病〉(“Vague de paresses”),首將穆杭小說譯介進入中國,開啟了中國新感覺派文學實踐的扉頁。然而,儘管法國小說家穆杭和中、日新感覺派小說的淵源受到了不少注意,穆杭早年奠立獨特風格的小說集《溫柔的存儲》(劉吶鷗譯為《溫柔貨》)中文譯本卻於晚近方姍姍來遲,終於登場。
《溫柔的存儲》1以三篇短篇小說組成,出版於1921年,書前收有一篇和小說篇幅不相上下的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序。這三個故事都發生在一戰後的倫敦──穆杭青年時留學於此──分別描述了三位異國女主人公:克拉麗絲(Clarisse)、德爾菲那(Delphine)、奧蘿爾(Aurore)的際遇。
.jpg)
《溫柔的存儲》中譯本,段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2/1)
穆杭善以一戰後歐洲大都市為背景,書寫顛沛流離的異國女性,且其中寓有深意。克雷彌爾在他對穆杭分析中,已經指出「穆杭(在其第一本著作《溫柔貨》中)已經是新興的收藏家,專事收藏天涯淪落人。」普魯斯特在他為此書做的序中也稱「還有許多潛在的女人」,正「心甘情願地尋求著克拉麗絲和奧蘿爾的輝煌命運」,他還稱道穆杭「充分表達了新事物」,從此世界看起來不同於以前。的確,通過描寫這些流落異國都市女子的遭遇,穆杭以速寫般的創新筆觸,刻畫了一戰前後歐洲人複雜的精神心態以及歷史現實,呈現了多元、多變之新時代的典型人物。不論是沈浸於收藏古董小物,將自己形容為大眾節日、善於交際的好友克拉麗絲、喪夫後逐漸虛無沈淪的青梅竹馬德爾菲那、成長於自然也崇尚質樸的舞蹈家奧蘿爾,她們在都市裡載浮載沉的命運除了象徵歐洲「大都會的破體」(克雷彌爾語),無疑也演示了作為穆杭所見的,無根漂浮的現代人尋尋覓覓、安頓生命的幾種情境。
短篇小說因其體裁短小,利於描寫轉瞬即逝的現代生活切片,一直是穆杭所偏愛的創作體裁。而為了捕捉現代都市的繁忙、緊湊,並直觀地表現作者主觀體察到的世界和感性,跳躍的斷句、不同名詞的並置、隱喻、聯想和暗示,極短的對話,也成為穆杭寫作的不二法門。如穆杭刻畫「不會老也不會死」的克拉麗絲(傳說小說原型人物即為香奈兒)收集無用的古舊小物、珠寶贗品,夢想打造一座假花花園;他描述這些「長物」是「無法想像的小東西,沒有年紀,從不完美,是野孩子的博物館,是瘋人院的好奇心,是因回歸線而貧血的領事的收藏。」因為克拉麗絲「喜歡障眼法的這種現代追求」。在這些排列、並置的如詩情境中,作者沒有點破卻不言自明的,彷彿是在時光如風火輪般將所有人襲捲而去、堅固的煙消雲散、華美的轉瞬即逝的「現代」,小物儼然時間的皺摺,身上隱隱蜷縮著所有的反叛、戲耍和不合時宜,體現著所謂的「溫柔的存儲」。
此外,現代的學者也已指出,和當時超現實主義、新興藝術家都頗為交好的穆杭,他筆下描繪的女性也如立體畫般,是極其象徵式的,精準再現了她們各式各樣的經歷。如在《溫柔的存儲》中,穆杭如此刻畫嚮往和世界融為一體、質樸生活的奧蘿爾:「奧蘿爾跑向我,像勝利女神那樣」、「她放慢了腳步,她如明月般的臉開始清晰,凸起的兩頰把她的臉水平地分成兩個部分,中間短短的鼻子挺起,像警犬的鼻子一樣動著。」通過幾筆簡短而又立體的描繪,穆杭極其巧妙地通過書寫外貌,折射了他筆下女主人公崇尚自然的心靈狀態。
曾為外交官,又旅居各地多年的「世界人」(cosmopoliste)穆杭獨特的文學風格,曾通過翻譯,在上個世紀初風靡了一代作家。然穆杭曾言:「文章只是一個夢」(l’écriture n’est qu’un rêve)。然在這如鏡花水月的夢中倒影裡,穆杭書寫異國/女性,鏡中反射的無非是自己與一代人;那看似夢一般轉瞬即逝的,卻又是作家心靈之眼所體察的實存世界。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這樣談論現代:「現代性是過渡的轉折、瞬間的短暫、瑣碎的偶然,此乃藝術的一面;另一面,則是永恆與不變。」又如香奈兒所說:「潮流改變,風格永存。」穆杭雖說寫作如夢,但夢朝起即逝之餘,作家以藝術的形式將之永存,又何嘗不是牢牢把握住了他的時代,創造了風格?儘管因二戰時的政治立場,穆杭而今在法國仍受爭議,但潮來潮往,穆杭自成一家的文風,亦可說是歷久彌新,跨越百年,在全球化更為緊密的今日此刻,從巴黎來到亞洲,再次與中文讀者見面,無疑為「風格永存」這段話下了最佳註腳。